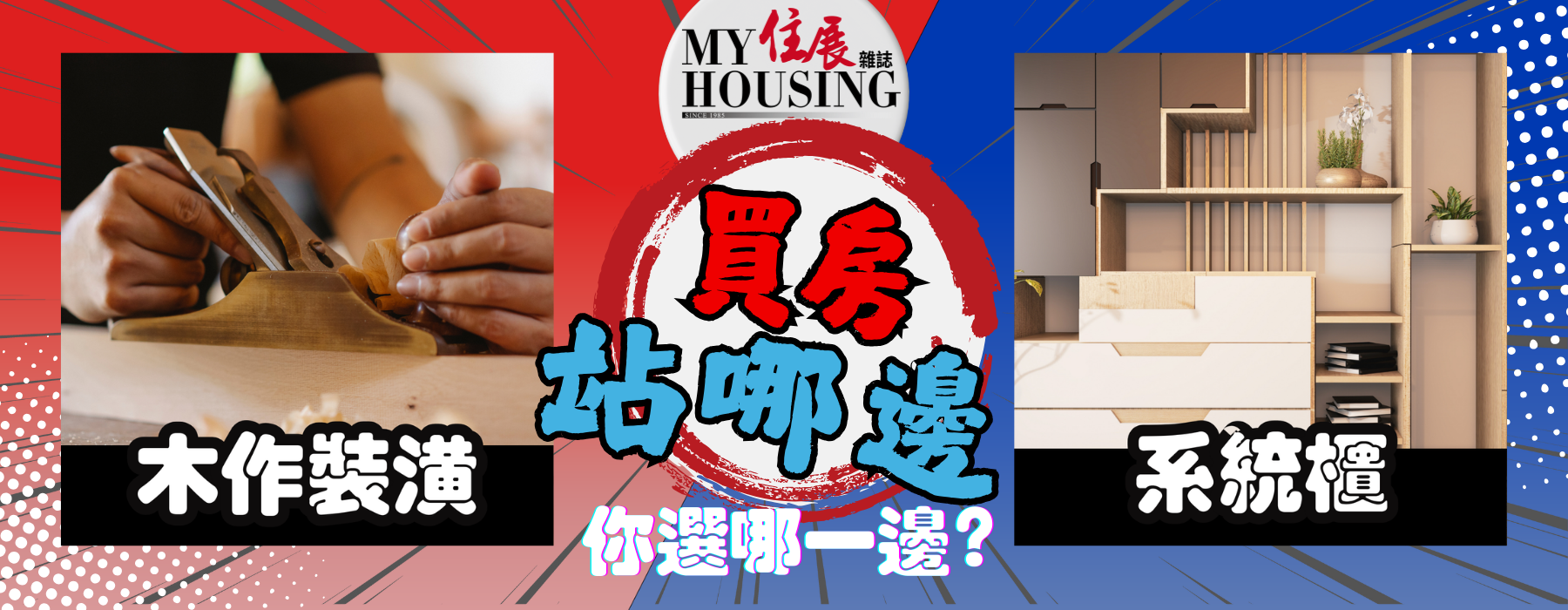「我是不想一輩子做同一件事的人。──邵唯晏」
在設計圈裡,邵唯晏的名字總與「原創」、「跳躍」、「設計整合」這幾個關鍵字並行。他是竹工凡木的創始人、交通大學建築博士,也是演講舞台上的講者、AI設計課的導師,更是空間語彙裡少數兼具批判與建構能力的實踐者。
文/朱福山 圖/竹工凡木設計研究室

若試圖將邵唯晏歸類為「建築師」、「室內設計師」、「跨界策展人」,似乎又都太小看了他。
設計師的養成,不在課堂,而在縫隙裡的叛逆
邵唯晏從少年時期起,就不是那個能乖乖待在線裡的孩子。國高中唸的是升學導向的高壓體系,讓他早早對傳統教育體制心生抗拒。喜歡畫畫、做模型,家裡卻說「藝術養不活人」,體育細胞發達,卻也被勸退體育路線。直到大學推甄開放,那一扇不看學科分數、只看口條與術科表現的門,成為他走進建築的轉折點。
他選擇了建築,不是因為出身背景,而是因為「門檻有彈性、好像可以畫圖、也可以動手做模型」,純粹是直覺,也是一點年少的叛逆。父親是大學教授,母親是家庭主婦,那樣的家庭教育,嚴謹卻又保留著某種沉默的自由。邵唯晏記得,父親總在深夜伏案疾書,某種知識的韌性與孤獨,也悄悄烙印在他心裡。
後來他唸建築研究所,再一路念到博士,主修的是當時還不算顯學的「數位建築」。那時候是2006年,他就已經開始研究人工智能(編按:當時AI尚不能稱為智慧)、HCI人機互動、參數式設計的關係,只是他沒想到,原本預估幾十年後才會落地的AI,十年內就成為現實。他常說:「AI不是要取代設計師,而是我們應該去和它對話、與它好好交流。」
「開,是為了和;通,是為了聚」

在他的定義裡,設計從來不是形式,而是方法論。他重視「差異化」大於「標籤化」,反對設計師被風格套牢。他說:「你看到某些作品就知道是哪個設計師,這其實很奇怪。設計應該像高定服裝,底層邏輯一致,但每位業主都該有自己的樣子。」這樣的論述,既對應他從小對規訓體系的抗拒,也映照他作品裡「打開又可收合」的語彙。
「誤用造物(misuse)」是他推崇的設計態度——不是錯用,而是有意識地跳脫慣性,重新定義物件、技術與語境的關係。這也說明了為何他能在中國大陸演講完一場,搭直升機轉場趕赴下一場,也能在戈壁演講後順便參加徒步比賽,意外拿下第八名。他說:「想多了都是問題,做多了都是答案。」
玩物尚志,大小孩的創作修練法


他是那種從不缺乏輸出的創作者:開課、寫書、演講、策展,但當被問起他的「輸入」從何而來,他卻笑說:「我生活其實很無聊。」最享受的是一個人看電影,喜歡最後一場、只有自己坐在黑漆漆影廳裡,那樣的沉浸與想像,是他給自己放空、也是重構思維的方式。這樣的矛盾,在他身上並不違和。他自認是「系統性地隨機」,表面跳躍,底層卻極度有邏輯,也回應了近來他所提倡的設計方法——可控的隨機。

而這樣的邏輯,也呼應他提出的理念:「大小孩」——我們都已長大,卻不該失去對世界的好奇與遊戲感。他曾出版一本名為《玩物尚志》的書,反轉自母親對他少年時「玩物喪志」的批評。他說:「我其實就是一個還想玩、還在學、還想試的大小孩。」

空間,也是設計者的自我折射
要理解邵唯晏,或許得走一趟他的竹工凡木台北總部。
這棟位於台北巷弄間的七層建築,不大,基地面積逾30坪,每層樓面積約20坪,但當你站在挑高的樓梯井,抬頭一望,會驚覺自己正同時身處三樓、四樓與五樓之間。
上下交錯的視角打破了水平平面與垂直動線的慣性想像,像一張空間拼圖,精準咬合又刻意錯位。邵唯晏說,他刻意營造出「空間尺度的混淆感」,就是希望人們進到這裡,不再用日常那套方式認識建築。
在這裡,每一處轉折,都藏有一個他對生活的再詮釋。例如他說:「樓梯不該只是連結樓層的空間元素,它應該是空間故事的起點。」

他特別指出一段藍色螺旋梯——一體成型的金屬板材經由電腦計算,再現場焊接組裝而成。這不只是結構工法的實驗,更是設計哲學的實踐:形式取決機能,工學藏於美學之中。樓梯踏板與扶手高度並非隨性,而是根據人體工學精算出最舒適的尺度,連螺旋盤旋的方向與顏色,都蘊含著風水中的「左青龍」之意。科學與文化、理性與趣味,就這樣在一段樓梯裡被他融合得剛剛好。
更妙的是空間的「可開可合」邏輯。像他的住家一樣,辦公室也是處處暗藏彈性——牆面可折疊、天花可打開、展演場域與工作區可互通。這不是一味追求開放感,而是他對「動態空間」的執念。他說:「開,是為了和;通,是為了聚。」空間不只是表層的材料堆疊,更是一種使用方式的演算法。你可以在這裡開會,也可以辦展、喝咖啡,甚至未來有機會開一間社區咖啡廳和買手店。
設計三種材料的樓梯,也設計出自己的切換節奏

他最喜歡那段樓梯:「有三種材質銜接,代表三段不同的設計思維。」這樣的轉換,不只是在材質,也像他人生的節奏——快速切換、清晰分段、卻又總能保持連貫。從中國大陸趕場回台灣、從演講舞台轉入圖面審校、從系統性邏輯切入空間美學,這些跨越在他看來從不是「跳tone」,而是「底層一致」的展現。他甚至笑說,自己是個「很會演的演員」,什麼角色上身,就能快速進入情境。
這也難怪,他能打造一個像「立體多維度的魔幻城市」般的工作場域,採訪時他帶著記者逛繞總部,這裡像極了重慶的立體巷弄,也讓人聯想到宮崎駿筆下那種「看不清哪是樓、哪是天井」的錯視世界。
但即使如此複雜,他從不誇耀這是「設計鬼才」的功力。他更在乎的是:「設計的底層是思維,不是形象。」他反對設計變成風格貼紙,更不希望自己被定義成「豪宅設計師」或「AI專家」,他說:「與其風格化,我更希望是去風格化,而追求差異化的生活方式。」
不被標籤的人,也不標籤空間
在這棟總部中,有一處展架,收藏著他多年的玩具與潮流公仔。那不是裝飾,而是他精神世界的物證。他曾寫下《玩物尚志》這本書,書中談設計,也談生活,談大人如何持續學習,也談社會如何逐漸抹去好奇心。

他說:「我不是什麼偉大的人,也不自詡為改革者。但我相信保持學習、分享思維,本身就會產生影響力。」他教AI課,卻總把「啟發性」放在技術之前;他做演講,卻堅持每場都重新準備、不複製,一場一小時的演講,他準備了近400張簡報;他帶領團隊,也從不問員工想要什麼辦公室,而是先創造出一個足夠有趣、能被生活填滿的空間。

有趣的是,他並不熱衷社群經營,網路上的他,大多是工作形象,卻反而累積了一群死忠粉絲。他說:「可能是我太常輸出,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要幹嘛。」但真實的他,其實很享受深夜獨處,喜歡無人打擾地看場電影,然後再把那些靈感、感受轉化為下一段空間敘事。
「與其想太多,不如多做一點」
對於未來,他說自己並沒有什麼偉大的夢想,但他其實已默默在執行:跨足教育、出版、AI、產品設計、策展、甚至有朝一日也許會拍電影。他說這話的時候沒有炫耀,而是一種開放的語氣:「誰知道呢?我們都只是大孩子,還在探索。」

他從來沒把設計看作是一條筆直的專業路,而是一個動態的系統,一種對世界的介入方式。他說:「設計不是服務於美,是服務於生活方式的轉變。」而這樣的話語,不只是理論,更是一棟棟被他親手打開、再重組的空間。
他不需要被定義,也不需要一個頭銜來框住自己。他只是持續設計、持續分享、持續玩,然後認真地——玩物尚志。

《住展雜誌》創立於1985年,是全台第一家房產媒體
擁有最豐富且即時的預售屋、新成屋資訊
以上文章未經授權,禁止擅自轉貼、節錄
官方網站:www.myhousing.com.tw
FB粉絲團:www.facebook.com/myhousingfan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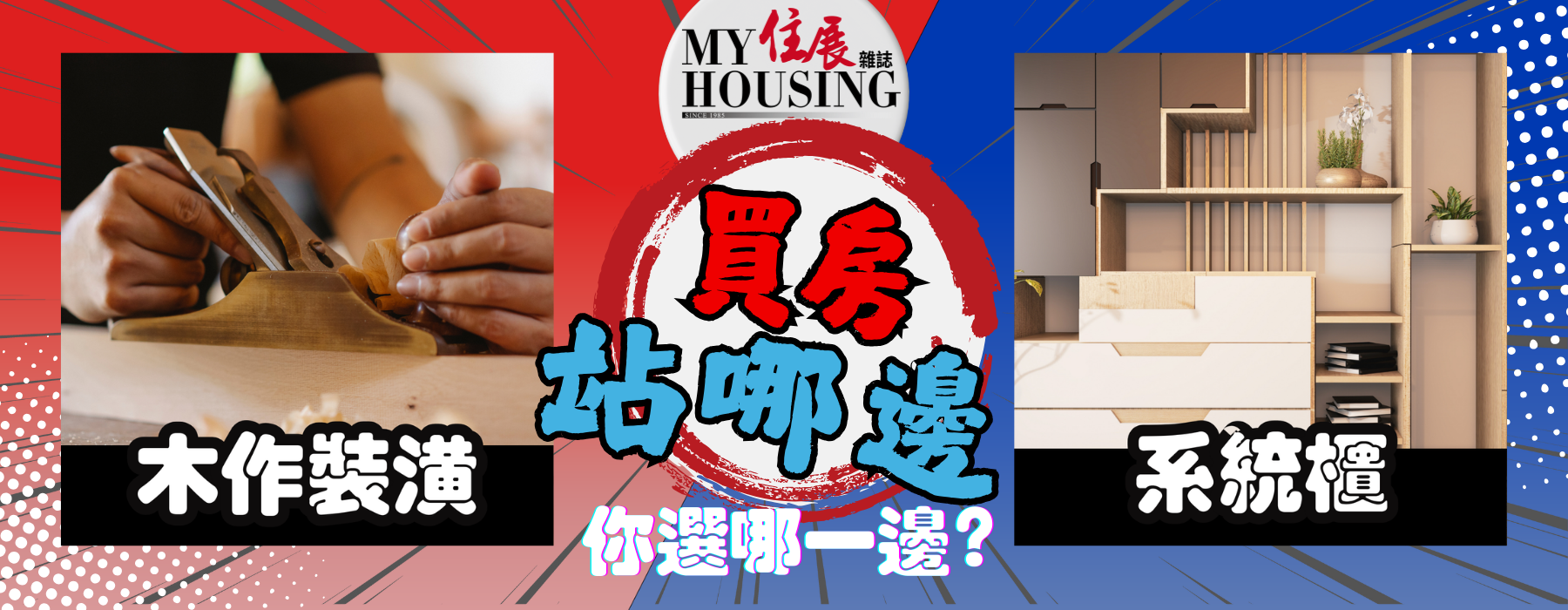
《住展雜誌》創立於1985年,是全台第一家房產媒體
擁有最豐富且即時的預售屋、新成屋資訊
以上文章未經授權,禁止擅自轉貼、節錄
官方網站:www.myhousing.com.tw
FB粉絲團:www.facebook.com/myhousingfan